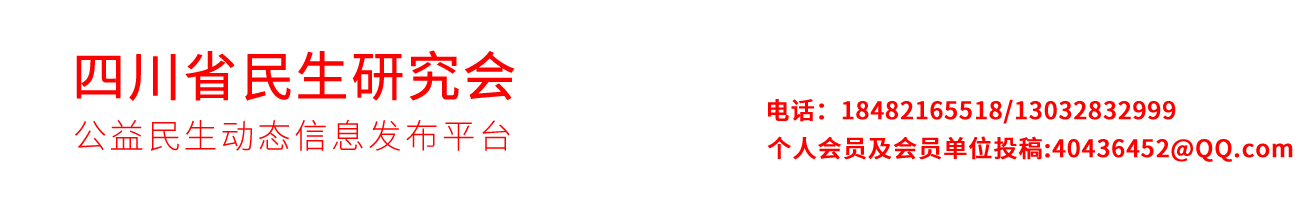文|黄少烽
吴永胜,射洪市作协副主席,四川小小说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射洪天仁公司。作品《皮狗》获第五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二等奖,作品《清明》获四川省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小说类一等奖,还著有《青杠岭山好捡柴》、《喜鹊》、《爆炸》、《九大碗》、《花儿与少年》等作品。作品先后发表于《百花园》《小说界》《小说月刊》《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湖南文学》《当代小说》《椰城》《飞天》等杂志、报刊。

较长时期以来,在小说创作中关于故事的问题上存在争论,我所知道的有两个极端情况,一种是不赞成小说中有故事,另一种情况是把小说写成了故事,而吴永胜却将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珠联壁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与探讨。
吴永胜是射洪目前小说创作十分活跃的作家,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原本是写故事的高手,曾经出版过一本故事集《变脸》,一共选了30个故事。故事内容包含责任、义气、亲情、使命、抗争等元素,这些故事画面感强,情节跌宕起伏,出人意料。作者通过描述小人物的传奇经历,特别是心理状态的刻画,反映人性的方方面面,读后令人深思。但后来,他觉得完全用故事这种形式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某些具有深度的思想与观念,于是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改为以写小说为主了。但他没有丢掉故事,他的小说有故事。所以我的这篇评论的题目是《他用小说讲“中国故事”》。
基层打拼的丰富阅历给与了他丰厚的回报
其实生活中的故事很多,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平凡的或者不平凡甚至稀奇古怪的故事,一直在那等作家发现。谁人能够找到它们,他就有了创作小说的本钱。吴永胜就很会在生活中发现故事,他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甚至捕捉到生活中闪光的、有意义的、能够用于小说创作中的东西,所以他就有了创作小说的本钱。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在选材上的偏好,和他的生活阅历、情感方式、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发现素材靠的并不是发现那一刻,而是你所有的积淀,你读的书、你的观察、你的思考。吴永胜由于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就能够慧眼识珠,能够在生活中捕捉到看似平凡却有意义、能够用于小说中的故事。
浏览吴永胜的小说,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或以淳朴的人物故事,或以乡村的个体沉浮,或以市井青年的情感体验,或以普通人物命运的哲理探讨,充分展现了川中农村与市井生活的多样性与广阔性。有人或许会问:“这个吴永胜哪来那么多写的?又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或者文学院什么的,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作品?”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创作只能靠作者的心血,琢之磨之,才能玉汝于成。应该说,吴永胜就是一个最完全、最彻底的扎根在生活中的人。他曾经对我讲,他还是一个小青年的时候,为了帮别人推销产品,就走遍了射洪大大小小的乡镇,甚至很多偏僻的小乡场的小街小巷都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足迹。他进过砖厂,下过煤窑,扎过钢筋……累过了,苦过了,晒过了,淋过了,风雨兼程,饥餐渴饮,没日没夜地东奔西走,在生活路上摸爬滚打二十多年,从原来的小工、杂工,终于当上了“带班头”,开始独立承包一些小活,直至眼下主政红红火火的“天仁”公司。
艰苦的岁月磨炼了他的意志,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他钟爱的文学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也变成了他小说创作题材的富矿。由于他几十年扎扎实实地沉入生活的底层,所以生活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用射洪另一位作家董泽永的话说,“他在两条赛道上奔跑”,既在“生活之路”走上了康庄大道,又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丰收。早在21世纪初,我就在报刊上见到过他的名字,后来通过董泽永的介绍认识了他本人。再后来,大约是2004年的一天,他请我在“子昂城”的城墙上喝茶 ,顺便带了一大口袋文学杂志。我一边喝茶一边翻阅杂志,那些杂志上都有他的作品,有小说,有故事,小说就有他的代表作《皮狗》。当我看到这些文学杂志都是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甚至有《小小说选刊》这样的权威刊物时,不禁暗暗吃惊,忍不住说道:“凭这些作品,你完全可以加入省作协了!”而且有点冒昧地表示:我愿意做他的介绍人。不久,他就成为了四川省作协会员,而且出版了短篇故事集《变脸》。继2018年出版《变脸》之后,相继又有《三先生》《三木有把刀》《镟磨》等小说在《湖南文学》《当代小说》《青年作家》上发表。近年来,他的创作更是进入了“爆发期”:《铁厂夜话》《老弟的决斗》《花儿与少年》《青岗岭上好捡柴》等数十件作品,陆续被《贡嘎山》《椰城》《飞天》《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嫁妻》《英雄》《绝猎百丈岭》等先后被漓江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年度选本收入。2024年5月,他终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
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来自于他生活的故乡,尤其是故乡的农村。他以写实为主,从生活的不同层面撷取题材,村舍、田边、乡村小路、乡土人情,农民的朴实与风趣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描摹人情世故,透视人心人性,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老弟决斗》有新写实的味道,观察生活细腻、准确,语言有—种绘画的质感(这有点像费尽贤);《九大碗》以—个小娃儿的视角,写尚在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对物质的渴求;《大蛇》表现的角度很独特,有新的观念,新的认识,他没有经历过土改,但他在小说中对土改却有独特的诠释,其中有的细节描写十分精彩;《青杠岭上好捡柴》表现的是物质、精神乃至情感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人的本能遏止不住对异性与情感的渴求,选择“人”或者“情感”还是选择物质成了摆在主人公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留给读者很多思索的空间;《喜鹊》表现一个农村少年隐隐约约萌动的情爱之心,城市少女的行为方式让他觉得新奇,使他受到影响近而被吸引。他的这种表现固然有对异性的向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其实这是一种进步,是向现代文明靠近;《青龙偃月刀》所写的主题说来不算新颖,但由于他很善于寻找独特的切入角度,所以就让小说“花样翻新”,从—个孩子想造玩具切入,把一个小娃儿的心态与另一个娃儿的冲突写得生动、细腻而逼真……看得出来,他的小说偏重于批判,对于传统的惰性和这个民族的某些消极面的批判,这些作品唱响了旧时代的挽歌,同时也表达了对新生活新时代的呼唤。
由于吴永胜的小说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他从生活中捕捉到故事后再经过认真的构思写出来的,所以他的小说不需要生编硬造,而是生活的自然展现。看了他的《青杠岭上好捡柴》,觉得他很会写生活中的细节,小说中的生话气息十分浓都,无论是人物的动作、心态还是对话都是如此。比如“喜鹊叫,喜事到”,这是生活中常见的一句谚语,但在小说《喜鹊》中,这句话被赋予了另一个意思,喜鹊叫对于婆婆来说是喜事,但对于春明来说却是令人伤心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为给小荷做“呱婆子”挨了打,而小荷却走了,还把“呱婆子”送给了水莲。小说表现了几个单纯可爱的农村孩子青春期的萌动,很有生活情趣。小说的语言也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像“春明,你害娃了么?核桃米米才一包嫩水呢。十月核桃九月梨,现在才八月。”“把板凳端过来,条子自己拿。”这类话很有地方特色与“个性化”的色彩。尤其是 “骨头敲断了,想让我继续白养你?换根细的。”这话,将一个父亲对儿子恨爱交加的心态表现得微妙微俏。在《九大碗》中,写大姑婆去世了,人们把她放在“门板”上,穿上“淀青色的老衣”,“脸上盖几页黄裱纸,鞋底点了七个墨点,下面座个烧纸瓦盆”,这些情状,都具有川中农村老人去世时典型的民间风俗特征。而为了做“九大碗”杀猪一段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杀一头猪的程序“捉、割、拿、扯、喂、捅、抽、捏、吹、拍、伸、倒、搅、淋、拈、刮”,正是我小时候在外婆家亲眼见到的情景。这些情景,没有对四川农村生活尤其是川中民风民俗的了解是写不出来的。
他善于将故事通过“改造”变成为小说的素材
生活中,有人对故事不屑一顾,仿佛小说中一写故事就降低了一个层次。也有作家认为,写小说,有无故事不重要,甚至觉得,短篇不一定要有故事。但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现在连一个推广文案都要从故事开始。我觉得,对于短篇小说来讲,有一个好故事在那儿,你写的时候底气会足些,好像有一堵结实的承重墙支撑着。当然,小说不是故事,但小说可以有故事,只是不能把小说写成故事,或者说,小说中的故事不止于故事,可以超越故事,深藏寓意。
故事能否成为小说,取决于作家的审美趣味。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说过:“编故事容易,写小说难”。著名作家张贤亮曾经在《怎样写小说》的讲座里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就是情节线加气氛,情节线就是故事,光看情节线,这还不是小说,小说还要加气氛——情节线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氛围、气场。所以只用光秃秃的情节还不行,你必须想到怎样才能让读者进去,因此气氛渲染也很重要。小说是要靠描写的,不是单纯靠叙述的。
生活之树常绿,文学的力量在于与生活的紧密却不是简单的联系,作家的智慧正在于能够从事件的深层、生活的深层、人的心灵深处触摸到生活的脉搏、历史的脉搏,善于将故事变成为小说的素材。
吴永胜正是这样,他善于在生活中寻找故事,但他也善于将故事变成为小说的素材。即使找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他也不会直接用于小说中,而是进行一番处理或者改造,根据小说的构思将故事分割甚至淡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他的小说中,不能一下子就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细心地把这些故事的碎片连接起来,就能够理清故事的脉络,甚至找到这个故事。吴永胜在与我交流《花儿与少年》的写作过程时曾经说道:“我以前热衷于讲故事,近些年读了些书,读了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作家汪曾祺的作品,有了一些领悟,对于一个文本,好故事只起到了支撑作用,血肉还是在作者的叙述搭建上。”《花儿与少年》最初也是以时间切片的方式讲一个事件,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波澜在平静的水面下起伏。这个特别要功力。
但对于故事中重要的东西,对小说有用的部分,他不会淡化,甚至要强化。比如小说的结尾,本来小说不一定有圆满的结尾,甚至可以残缺,可以给人留下遗憾,而故事的结尾却要有惊人的意外,要令人回味。永胜怎么办呢?他发扬了善于写故事的优势,为了小说的可读性,他将故事的结尾方法保留在了小说中。2022年5月,他将小说《青杠岭上好捡柴》发给我,看了小说后我觉得很沉重,我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无论是物质、精神乃至情感都是极度匮乏的,然而人的本能又遏止不住对异性与情感的渴求,选择“人”还是选择物质,这就发生了冲实,这是很艰难的选择。这个小说提供给读者很多思索的空间。虽然我觉得马女子的眼睛被家安扎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有些牵强,但其动机却带有合理性。我认为这篇小说的开头不错,但结尾是太草率了,缺少意外之笔,不够味。他叫我支招,我就在微信上说可否处理为让家康出走,这一走让马女子终于意识到她想得到家康是不切实际的,最后以“谁把我的眼晴整坏了的我找谁”为由,仍委身于家安,这样也符合她的性格,也最终有了一个合理的结局。我因为那几天眼睛不大好用,拖了几天才把我的意见发给他。他可能等不及,就先把稿子发到《四川文学》的副主编卓慧的邮箱了。第二天早晨收到我的意见,我提的本来也只是一个思路,供他参考,谁知他却十分重视,又把稿子撤回来了。他在微信上对我说道:“卓慧曾经说这个稿子的结尾太过散文化,我一直理解不透,不知道怎么修改。看了您的建议,我明白了,其实就是结尾没有‘翘’起来。之前我只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家安兄弟有了矛盾,这矛盾便成了另一种悲伤。现在,我根据您的意见,是这样计划的:家安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我会想出一个最合适的处理方式,故事的发展始终要贴紧人物,最后的结尾,一定是家安这个人物的完整和完善……”他在创作上的严谨与努力,可见一斑。
他的小说中有故事但超越了故事
2021年5月6日,我曾经以个人的名义邀请吴永胜和写小说的魏源水、李太贤等在“思和院”讨论他的小说,大家对他的小说是充分肯定的,一致认为,他还是关注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但同时又不拘呢于传统的表现手法,而是向现代派的文学吸取营养,大胆探索,勇敢创新,学习“先锋、新锐”文学的一些手法,使作品具一种新鲜感。
我也觉得,吴永胜的小说虽然有故事,而且有的还是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但并不觉得板滞或陈旧,因为他不局限于故事,更不是照搬故事。故事是反映大众关心的问题,表达大众的爱憎、情感,主题鲜明,易懂。而他的小说表达的是个体的情感、内心或观念,主题比较含蓄、隐蔽。这就是有的人读他的小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读懂的原因。我觉得他的小说虽然没有通俗小说那么具有传奇色彩,没有那么多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但他的小说是厚重的,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性很强的、特别是一些敏感的题材,他在切入角度、表现方法以及分寸感的把握上,都显得成熟与老到。正如前面所述,他不会直接把故事用于小说中,而要根据小说的构思对故事进行一番处理或者改造。
我们说的作品的构思可以比作工程师的草图设计,只有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能大兴土木,挖基开槽,一砖一石地盖楼建厦。一个好的构思会使一个故事变得很新鲜,很有价值,好比一种酒,这种酒或许各处都有,甚至不知名的小酒厂也生产得出来,但如果用一个奇特而精妙的瓶子装起,这个酒就可以身价倍增。他的很多小说也是这样,里头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好像其他人也能能够编得出来,但他通过一种巧妙的构思来使用这个故事,再用一种机智而有韵味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就使我们觉得这个故事有了一种味道。或者说自直白一点,通过这么一弄,他就把故事变成了小说。这方面,吴永胜与董泽永有共同点。
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题材和表现手法为其主要特征,集中书写和艺术描写了乡村图景及底层人物的生活真实。在小说的写法上,他摒弃了人为的戏剧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对生活的本向还原。他将情节作了新的组合,回忆与补叙穿插,视角的多变,日常生活细节的渲染,使主观感受的东西成为加强真实感的一种手段。我在题为《小说创作手法多元化的可贵尝试》一文中,曾以《花儿与少年》为例,评价吴永胜的小说“故事结构精致巧妙而不露痕迹,语言洗练、准确,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一种浓重的实录生活的意味……”
但吴永胜的小说也有不足。通观他的小说,就写农村题材而言,都是写改革开放之前的,诚然,那时也是新中国时代,也是可以写的,但一部好作品应该是一次对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庄重的、动人的、具有预见性的发言,应该成为旧时代的丧钟和新时代的号角,成为报春的燕子。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央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又提出了乡村振兴,农民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面貌还是观念都与以前大不相同,我们期待永胜关注这种历史性的巨变,并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巨变,写出更多更新更感人的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黄少烽,射洪市作家协会、陈子昂文学社、陈子昂诗社顾问,陈子昂研究会名誉会长。2022年入选射洪市首届“文化名家”。(来源:遂宁市文联)